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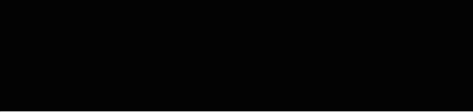
考完了研究生,很多人见面就问我:“你考上哪个专业了?”我说:“文艺美学”,“那你这个专业毕业以后是干什么工作的啊?”我愣住了,每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很难解释清楚学文艺美学到底能干嘛,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专业的存在本身就不是为了干什么而存在的。但人们的思维定势就是:你学一个专业,就意味着你将来一定会有你对应的工作,否则,你学它干嘛?而我当初选择文艺学,就是凭借着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但如今这份爱,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却无比尴尬……
如果我在这里大谈特谈文学是“无用之用”,肯定有人说我故作清高,故弄玄虚。相反,如果我列举文学的诸种功用,纵使我绞尽脑汁举出千条万条,也不如人家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来得实在。
读了四年的大学,从刚进大学到匆匆毕业,每一个大学生在面对大学生活的时候无一不感到茫然,而这份茫然的纠结之处就在于:大家都急于想知道自己毕业后的出路,想学到有用的知识,而当自己在大学里所作的事情难以找到一个最终用途的归宿的时候,价值焦虑成为了每一个学生不得不面对的处境。
而这样的焦虑在文史哲类专业的学生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以至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现象:一方面享受着作为古老的专业的自豪和骄傲以及多彩文化世界的悠哉闲适;另一方面,则在就业取向和选择上,力求挣脱专业的束缚,摆脱掉文学的帽子。一时间,相比于其他专业,“学了四年母语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学”,成为了每一位中文毕业生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作为一个读了四年汉语言文学本科的学生,对“文学之用”这样一个问题,我肯定有我自己的答案,并且坚定不移。但这样的一个本应该坚定不移的答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却显得如此多余和软弱。这背后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偏差,更是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异和畸形。
或许,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已然成为一种历史的无意识,一种完美无缺的但却必须悬置起来、藏匿和掩盖起来的软弱无力的象征。在现代的社会中,文学仅仅是一个被指定了的符号,一个不断被社会阐释的称谓,而文学的真正存在却在这形形色色的阐释和解构中永远封闭在一片盲区中,永远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文学的尴尬局面不仅仅在于在“文学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上的那种懦弱和难以言说,更在于这种现象揭示着社会历史背后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骗。
一个“用”字,如果我们不把它仅仅视为一个纯粹理性意义上定位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其概念最重要的内涵是由历史规定的。没有人会否认,文学这样一个博大精深而又古老的学科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毕竟,在遥不可溯的远古历史中,就在那个生殖和繁衍后代不再是种族生存的重要依凭、古老的人民开始在黄河流域过上定居生活的那个年代,文学就已经留下了一些无声的零星的残片。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有趣的事实出现了:虽然人类文明的起源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但时光流转,万年过去之后,在机械复制时代今天,那个曾经诞生了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学问如今却成了一片“旷野上的废墟”、一种“空洞的能指”。
相信在未来时代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20、21世纪之交的我们民族经历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一定是一个百思不厌、回味无穷的瞬间:国门洞开,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渐渐模糊了多种选择之间的界限。“文学已死”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已经使得文学的出路异常艰难。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一个功利心极强的社会则注定将是文学的坟墓。
在现代社会中,确立“文学”与“用”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确立物质精神存在与文化符号称谓的关系,几百年来文学作为一种非主体、非中心的标志之一便在于:不仅仅文学主体内在的承载物——语言文字,割裂于社会实用价值体系之外,而且文学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传承的外在功能价值也被割裂于社会中心的视角之外,被操控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当今,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文学是一个热门学科,而社会生活也不会再像五四时代那样因为文学界的某些声响而为之震动,商品化社会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学的“边缘化”时代的到来。
商品化社会能够传达而法律条文以及伦理规范未能传达的一种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人们的欲望以及对欲望的实现,人们的价值取向中也流露着某种欲望象征化的过程。商品化社会与其说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欲望实现的可能得以最大化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着某种“成功”,追求着某种个人欲望的满足。与之相反,凡是与这种“成功”无缘的价值选择,都被作为一种“无意义”而被悬置。
对于“成功”内涵和外延的定义,或许找不到标准的语言表述,但它却能够非常明显而且直观地的体现在人们人生道路的选择上。
于是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我考研上,中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考研人数逐年升高的形势下,2007、2008年的报考人数突然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考研究生出来有什么用?毕业了以后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么?”,似乎高等教育的出现最终必将要以市场为导向,而人们考大学去学知识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工作。即过程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过程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类似的现象已经在我们中学时代就出现了。曾经,许多媒体就“高考应不应该进行文理分科”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无论最终结果怎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多年来,在“文”与“理”两条本应该并行不悖的道路选择面前,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后者。“学文有什么用?”成了每一个做出这样选择的人所质疑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问题,因为至少在他们看来,“文”学除了整天埋首于故纸堆中喊着之乎者也之外,没有其他的实际价值。
从另一个侧面讲,在面对“文”、“理”两条道路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首要的选择出发点并不在于“文”与“理”本身的价值大小,而恰恰在这之外。
“文”与“理”两条道路,正如中国广阔疆域上的黄河和长江,一条,孕育出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浩浩荡荡承载者中华民族的历史奔腾不息却无人了望,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象征而已;另一条,九曲回肠绵延东去,同样古老却常流常新、造福两岸,为人们真正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惠。人们不会否定黄河作为“母亲河”的神圣地位,但却不约而同地趋之若鹜一般选择来到长江三角洲去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在中国的教育理念中,有一种观点可以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都会或隐或显地被家长灌输的思维模式,即:“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然后就能找个好工作,然后就能赚大钱,过上好日子。”换言之,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文化知识的学习的目的和结果只有一个,至少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话很实在,也很到位,因为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过太多痛苦的、饥饿的回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它其实一语道破了人生中生存挑战和幸福生活的矛盾,而且唯一有可能化解这一矛盾的,就是一个字,“钱”。
如果说“拜金主义”是一个令我们人人都摒弃的极端龌龊的思想的话,那么,“实用至上”或许可以将这样的一种极端柔化到我们可以原谅的程度: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不必处处都考虑钱,但一定要“学有所用”。
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因为它毕竟是我们考虑问题时候的习惯性思维,也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节奏极其迅猛的时代所必须学会的思维方式,即:“没用的事情,我不做!”。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升学、就业的压力的时候,任何急功近利的、私自的正当想法都是可以原谅的,正如许多中文系的学生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本专业,其解释就是:“我想学一些更加有用的知识”。这样的价值取向或许不仅不应该摒弃,而且值得适当提倡:立志于做“有用”的事情肯定不能算是错事。
但是,这样的一种“实用至上”的思维方式其背后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生活中某种具体的生存技能的话,那么上大学或许还不如上专业技校来得实在,因为大学里面学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比如,文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学会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的精神生活得更充实。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第二,正如清华大学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讲过的:“言有易,言无难。”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有”,这很容易做到。但要说“无”,则必须看到所有东西才敢说。谁敢说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呢?这太难了,所以,你可以说文学有用,但如果说文学无用,或许还差点资格。第三,事实证明,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劝自己日后准备经商的孩子们在本科中放弃企业管理,改学文史。
但悲哀的是,到了今天,这样的价值选择不仅没有得到矫正,而且还越来越重。举个例子,在恢复高考后的头三年,北京大学文科最高录取分数是中文系,理科是物理系。可惜没过几年,中文系就成了没用的系,录取分数直线下降。好学生都跑到经管、法律等专业去了。如今北京大学录取分数最高的学院却成了光华管理学院。
我只能说这是北大的悲哀,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也是这些学生的悲哀。为什么要说的这么严重?因为作为法学、工商管理等专业,它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谋生技艺,至少以后有口饭吃,如果一个人才能平平,胸无大志,学这些专业也许尚可。但是,考到北大的数一数二的人才,理应是时代的精英,他们涌到这里来的原因又何在呢?难道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心里想的不过是有口饭吃?
事实上,一个人最关注的是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只关心自己下个月会得到多少工资,那么也许你这一辈子都会为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但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社会公正,你就更可能成为领袖;如果你关心传统文化、审美思潮,你就有可能成为哲人和智者。只有一个研究社会,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许许多多人建立强有力的纽带,为人类和社会造福。
原因也很简单,按照马斯洛的心理学说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一般而言,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获得满足。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需求。
北大清华在中国的地位,恐怕要比哈佛在美国的地位还重要,北大清华每年都能网罗全国各地的“第一”的学生,按说,这些“第一”应该是时代的精英,是未来的领袖。他们越是“第一”就越应当关心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而当这些精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学市场营销,仅仅为了将来能混碗饭吃。这样下去,中国的将来会怎样?
需要明哲保身地说明的是,在这里拿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进行比较,目的并不在于要取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用”价值,因为没有人会否认这些学科存在的意义。但是,在这里更要强调的是,无论将来是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职位,我们必须明确,其最基本的“根”都在文史哲。文学阅读中的诸多技巧,如批判性的阅读、破解既有的叙述、解构叙述特权、发现被压抑的叙述者的声音、通过感情移入理解他人等,都是认识人和社会最基本的,又是学无止境的技巧。不管以后从事什么事业,首先要懂得如何解读生活的文本。这是才是精英的教育应该学的根基。
我们常说:“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知识一定要被应用到实践中才叫有价值。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奉之为真理的话难道真的是正确么?或者说,难道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在实践中才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么?如果理论脱离了实践,那么,理论就没有价值了么?
理论如果不能给实践以直接的指导,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失效,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否为指向当下实践和历史确立基本的价值标准、思想规范、立论依据、阐释视角。换句话讲,知识的与实践的隔层,不仅不是它的失职、失效,恰恰是它应有的价值功能的正常发挥:只有知识的抽象概括、间接阐释,才能使其与实践层面、功能层面区别开来。才能真正以一个审视的、客观的、冷静的视角看待现实。
作为一个孩子,他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不应该是将来我要靠什么吃饭,而应当是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有非常大的好奇和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
“百无一用是书生”,千百年来,文人们这样一个“无用”的形象从战国时只会纸上谈兵的赵国名将赵括到鲁迅笔下那位只知道茴香豆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话的笑柄。文人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不将金钱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目标,而是自己沉溺在自己建构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乐。因而古往今来有关迂腐文人的笑话层出不穷,文人逐渐成了寒酸、懦弱、固执的代名词。
事实上,自古文人爱财如命者有之,是金钱如粪土者有之,“书生”是根本没有必要忌讳谈“钱”的,正如鲁迅所讲:“对于那些反对钱是万能的人,你按一按他的胃,里边肯定有没有消化完的鱼和肉,饿他三天,他就不会说了。”
食色,性也。物质追求是每个人生存所必须的基本追求,追求基本生活保障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追求物质,而在于你是否将物质当做你最高层次的追求?正如邓拓所讲:“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尤其是当社会处于转型时,当民族处于危难之时,精神层次的支柱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其实根本不用去证明,早在1918年,鲁迅“弃医从文”选择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了。鲁迅的选择实际上是一次“回归”,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消实用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取消那一个社会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在文化还未与时俱进的境况下企图通过实业来救国的可能性,取消了那种仅仅“治标”而不“治本”的振兴民族的方式。这也是我们衡量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正确与否的标准。
自然科学是治标的,而人文科学才是真正治本的!
如果说当年鲁迅的选择是以当时“愚弱的国民”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为前提,是对那样的特定的一个动荡社会的一次治疗和挽救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难道就不再需要进行精神疗伤了么?
社会发展表面上是严格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但几千年来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属于上层建筑文学的发展恰恰不会完完全全跟经济基础保持同步,就像当今的科学水平、政治制度尽管远比古代时候发达,但当今的文学水平已经远远不能跟悠远灿烂的古代文学相媲美了。同样地,如果我们将文化剖离出来,就会惊异地发现:虽然现在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远高于“五四”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五四”时代何其相似!因此,鲁迅的“弃医从文”的选择不仅选择了那个时代,更是选择了百年后的“未来”。
1993年,《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引发了一片讨论。所谓的人文精神危机,就是指在我们这样一个价值观念大转换的时代,信仰、信念和心跳无一不受到怀疑、嘲弄,创作上大多是媚俗和自娱,没有自己的信仰,不得不依附外在的权威,只能取悦于公众来糊口。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渐减少,作家和批评家选错了行当。“下海的”人越来越多。
在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同时,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施压,导致了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的枯竭。
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三个对抗:人文精神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以及科技主义相对抗。一般来说,人文精神是对人性、人的价值的全面关怀的思想观念,但这太笼统;具体说,是对人性的全面关怀,对人的全面价值,尤其是精神文化价值的格外重视,不仅给予现实关怀,而且予以终极关怀的思想理念;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强调人文学科、人文学术领域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今天的文化现实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处在深刻危机中。当代知识分子乃至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表现。知识分子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这种精神失据,并非个人和最近十年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各种因素合力而成。要想摆脱这种失据状态,绝非一个短时期能够做到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作为努力的开端,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实践这种需求精神,即“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时间是一个不断成长和丰富的过程,体现了其充满充沛的活力。
最近几年有关《红楼梦》的讨论多了起来,出现了一股“红学热”,于是有人讽刺到:“《红楼梦》就这么一本书,养活了多少个红学家和文学家啊!”在说笑之余,可以看到,这样的讽刺的内在前提是,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统统扔掉,就留下其“实用价值”之后得出的结论,即:《红楼梦》能供人吃饭!显然,这样的价值评判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低级的、庸俗的。如果这仅仅是无聊人的一种说笑和讽刺也就罢了,但问题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评判却得到了大众的认同,被视为“精辟”、“到位”之论。可见,审美文化的当代流变已经再以我们不可想象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两年前,人民大学美学教授余虹的自杀令我震惊,因为我清晰的记得我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听的第一场讲座就是他的《审美文化的当代流变》,当时他在现场作出的振聋发聩的疾呼令我震撼。而面对如今的这样一个社会,我只能说三句话:1、你只能从个人的现实体验出发去追求终极价值。2、你能追求到的,只是你对这个价值的阐释,他绝不等同于这个价值本身。3、你只是以个人身份去追寻,没有谁可以垄断这个追寻权和解释权。.
杨宁撰文于2010年07月18日
Copyright© 2020 文化传播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